在广东,有这样一片区域。
它突破自然常规。广东大河多向南流,梅江偏一路逆行东北,半途又顺势南折,在大地刻下45°的凌厉尖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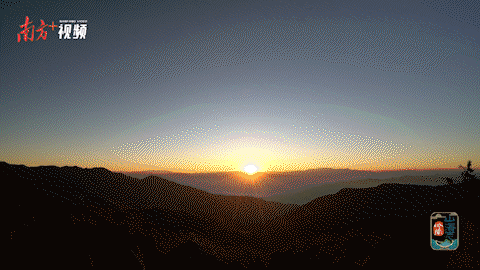
它在方言上自成一派。粤语、潮汕话、闽南话的“十面埋伏”之下,这里仍留存着一口中原古韵。
它敢于重新定义故乡。

中国人崇尚安土重迁,这里的人们却将“客”字深植基因。
梅州,为何群山封不住?
去远方
客家人的流浪始于一场王朝的瓦解。

西晋末年,为躲避战乱与奴役,中原先民首次集体开启“生存模式”,裹着烟尘一路向更深、更险的南方山地辗转,史称“衣冠南渡”。他们也因户籍册上的“客籍”身份,拥有了全新的名字——客家人。
而这场大迁徙的落脚点,最终选在了梅州。

为何是梅州?让我们从地图中寻找答案。
梅州,八山一水一分田,由华南褶皱系的宏大构造与多组断裂带共同塑造,武夷、莲花、凤凰三大山脉于此层叠斜卧。山脉与山脉间的低谷并非富庶之地,却是战乱时代的天选避难所。这,便为客家人留出一道生存的缝隙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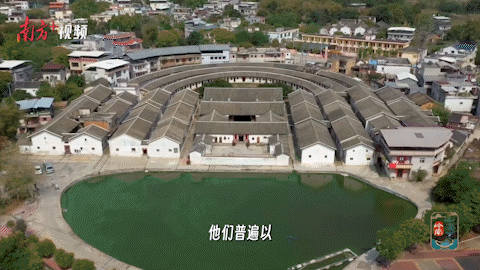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,远行的族群终于在此安顿下来,诗书继世,耕读传家。他们普遍以“第”“围”“庐”“堂”来命名自己的居所。居所的堂联上往往写着“荥阳世泽”“颍川世德”等,以此纪念回不去的中原故乡。
但如果你以为他们就此止步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此后,他们又从梅州动身,下南洋、遍全球,探寻世界的步伐从未停歇。

1859年,18岁的张弼士从这里出发,数十年后成南洋华人首富,更以回国创办张裕酒业为开端,成为近代实业救国之先驱,被《纽约时报》誉为“中国的洛克菲勒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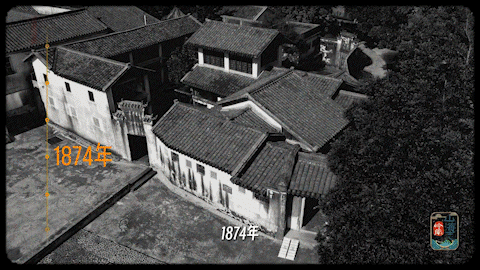
1874年,26岁的黄遵宪从这里出发。从北京辗转日本、美国,高呼着“万国强由法变通”,推动着政界维新和诗界革命。

1917年,12岁的李惠堂从这里出发,经香港远赴日本、东南亚、澳大利亚,成就一代球王传奇,带领中国足球队首次挺进奥运会。
1963年,29岁的曾宪梓从这里出发,辗转香港、东南亚,以一把剪刀创立了享誉世界的“金利来”品牌。
“客籍”底色铺就远行之路。正如从这里出发的林风眠。一生以浮云孤鹜、山石笔墨,绘就客家人的淡淡愁绪与不屈风骨。
植此根
经历上千年的迁徙后,客家人把文化象征凝固成独一无二的建筑形态:围屋。

它们有的圆,有的方,有的又圆又方。圆,展示着持经达变的柔和;方,则象征着坚守本心的刚直和大义。
丘逢甲故居就是这样一座方圆并存的围屋。1894年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丘逢甲这位生于台湾的客家人刺血上书,要求拒倭守土。在抗日失败后,他渡海回到梅州老家,在此写下了“四百万人同一哭”“去年今日割台湾”的泣血之句。

今天,站在台湾光复80周年的历史关口,客家先贤的风骨依然在海峡两岸激荡出深沉的回响。
除了家国大义的底色,客家文化中还处处透露出一种刚柔温猛、古今中外的杂糅之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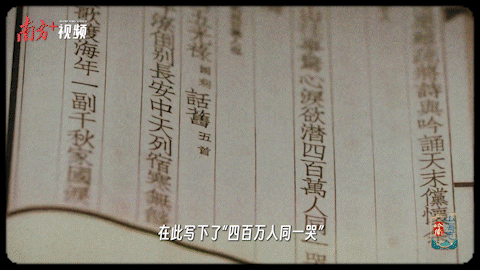
语言上,主打一个混搭。既有《诗经》的古雅,管“河边”叫“河漘”(chún);又秒变翻译鬼才,给“sofa”硬加上一个“凳”字——“沙发凳”三个字,写满了既要洋气又要让你听懂的倔强。

饮食上,将刚柔哲学端上餐桌。方寸豆腐棱角分明,却温柔地包下圆融的肉馅;炒热的粗盐以烈火之势围堵,反而逼出鸡肉的嫩滑与汁水的丰沛。

娱乐上,把亦张亦弛玩到极致。

这里平均每4个人就有1个会踢足球,每一万人就拥有2.6片足球场,“足球之乡”的称号实至名归;而当山歌响起,又是另一种画风:那即兴对唱的《诗经》遗风,不仅是国家级非遗,更是客家人刻进骨子里的文化条形码。
淬烈火
梅江、汀江、梅潭河,三水汇聚成韩江,撕开一道峡口向南奔流而去。三江汇聚处,便叫三河坝。

1927年10月1日,朱德率领三千余人在此阻击敌军,为掩护南昌起义军转移争取时间。三河坝战役后,朱德重整军队,折返向北,最终实现了井冈山会师。梅州以自身的浴血奋战,保存了起义军有生力量。

后来,梅州依然以山为骨、以河为脉,为革命开路:这里是原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,中央红色交通线的生命节点;也是闽粤赣边区的战略支点,边纵铁流的成立之地,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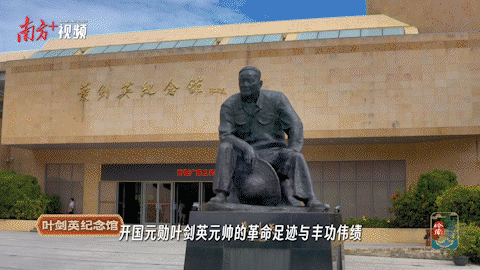
开国元勋叶剑英元帅的革命足迹与丰功伟绩,更是被永远镌刻在这片红色土地上。
开新篇
梅县松口古街上,一座五层洋楼静立了近百年。

昔日,不少客家人下南洋淘金或归国探亲时,都会在这里住上一宿。如今,他们的故乡早已不是陈旧的模样。
旧港务所被打造成“松口印象”主题酒店,乡村咖啡、宝藏书店和汉服体验馆上线古街。

这股名为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的新风,为梅州带来一条又一次走出大山的新路。
这条路,不是对大城市的机械模仿,而是培育一种梅州独有的新活法。

在县域,它是老树发新枝,一县一赛道。梅县的工业老树嫁接上了智造新枝;兴宁的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等产业“握指成拳”;蕉岭的长寿之乡成为“周末好去处”。

在镇村,它是旧貌换新颜,一镇一风韵。兴宁市黄槐镇从煤灰漫天到军旅新风,实现“黑色”到“绿色”的蝶变;蕉岭县麻坑村让废弃老厂化身数字创意园,完成闲置资产到创新引擎的价值重塑;漫山遍野的金柚,则借助电商直播真正香飘四海……

随着梅龙高铁在山间呼啸疾行,梅州人可以更轻易地冲出大山,与大湾区相融,与更广阔的天地相连。

迁徙千年的客家人,终于给出了第二个选项:
归来,也能抵达远方。










